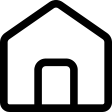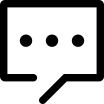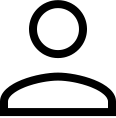本文转自:济宁日报
按快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杨进峰
自从手机有了照相功能,人人都成了摄影师,每天的生活点滴或美景随手一拍,就能发朋友圈或抖音上晾晒,但这些照片多少有些违和感。这远不是拍摄技术和装备优劣问题,而是隐藏着对于摄影的文化的理解。
我是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。1975年,舅舅从部队回家探亲,行李中就有一部照相机,他带我去田野照相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几乎没人照过相。那时我7岁,不懂照相是什么意思,却因为好奇而兴奋得不得了。
舅舅回部队后,我天天盼着照片邮寄回来。大半个月过去了,收到舅舅的来信,全家人围在一起拆的信封。除了舅舅写的信,里面还装着一张我的黑白照片。
我的身影竟然在一张纸上,这也太神奇了。从那时起,我就一心想要一部照相机,也能像舅舅一样,把镜头对着人按下快门,将人的身影弄在一张纸片上。
然而,长大以后越发觉得摄影之梦的艰难,一个农家孩子,根本买不起最廉价的照相机。但我内心中有一百个不情愿,暗暗发誓,我一定要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。
上高中时,我省吃俭用,在学校食堂打最便宜的饭菜,一心想从伙食费中省下钱。终于在高二第二学期,省下来15元钱,买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照相机。那台相机,是从县城地摊上买的,但我如获至宝。因为买不起胶卷,拍每一张都是谨小慎微,而且常去县图书馆借阅摄影方面的书籍,逐字逐句地认真钻研,记了几大本摄影技巧。每个节假日,我都要背着这部塑料壳子的照相机,寻找和记录我认为耀眼的人或事。
18岁那年,我参军到了部队。不到半年,就用积攒的津贴买了一部当时还算高端的相机。我常去捕捉工作和生活中最艰辛或最有意义的瞬间,我还将有新闻价值的照片配上简短的文字说明,投到军报和当地报纸,竟然有许多被刊用了。当兵的第3年,我在报刊发表的新闻图片竟然有上百张,被推荐上了军校。
毕业后,团里任命我为政治处宣传干事,为我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机。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,团里的简报、宣传专栏、连队的训练剪影……到处留下了我的摄影作品。
我在部队的第17年,团里要编撰《团志》,我用相机记录下的部队抢险救灾、追捕嫌犯等系列照片,被分门别类地刊用其中。
2003年,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当地几家新闻单位向我抛来了橄榄枝。到了单位,我第一年就考到了记者证。我奔赴贫困山区,拍摄了大量照片。每每看到我在拍照,就有老乡喊我,“来,文化人,到我家喝点水。”虽然互不相识,但很是亲切,我从他们的脸上拍摄到了淳朴和善良。
我用相机记录着人间的友爱,记录着勤劳和勇敢,记录着生活中最为靓丽的风景,有摄影作品数万张之多。但我觉得,真正反映时代辉煌和有珍贵意义的却很少。我越来越觉得,按快门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我希望自己按下的快门,能够讲述历史,能够映照人文、叙说沧桑、见证梦想,让人看到照片背后的故事。